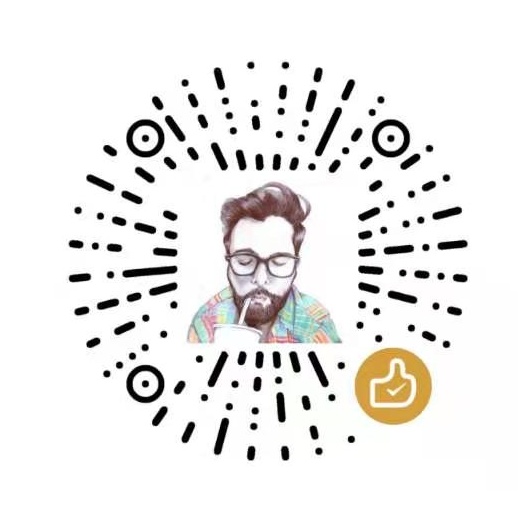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关秀丽知道,她有可能在裁决生死。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是每一个医护都要面临的拷问和抉择。她只能做到相对公平,测氧饱和度、看心电监护,把稀缺的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也是病情最重、难以挽回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一篇报道。
红会医院位于汉口的香港路上,离汉口火车站2公里,离华南海鲜市场也是2公里,还是120、110定点医院,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正因为这样,急诊科医护们各个身经百战。他们接过枪伤的、刀伤的、车祸的、心梗的甚至被雷劈中的病人,遇到过急诊室劫持事件,常年与流浪汉打交道,冬春季节接诊很多呼吸道患者,夏秋季节则收到更多不爱喝水的结石病人。
关秀丽今年41岁,工龄22年,是这个科室里最资深的员工之一。她个头挺高,马尾扎得紧紧的,说话爽利,带点黄陂口音。每天早晨7点离开家,走15分钟到医院,穿过门诊长长的走廊,道路尽头就是急诊科。12张床,28位同事,急救室门上绿色的大字,留观室里天蓝色的帘子,是她18岁之后最熟悉的世界。
按照计划,大年初一值完最后一个班,关秀丽和丈夫、儿子将飞到新加坡过新年,这也是她第一次出国,儿子马上就要上初三,她想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孩子一个轻松的假期,也很早就从医院拿回了上交的护照,看起了机票。侄子在新加坡工作,会为他们安排好旅程的一切。
之后的日子里,警报声越来越刺耳。关秀丽记得,那神秘的白肺,「过了两天,我们这儿也有了,再过两天,哎呀,怎么又有了。再过两天,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也感染了。」急诊科从以前的每天不到一百个号,到一天两三百,全是看同一种病。最开始还按照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排查,后来发现根本不对,有的人没有接触史,一样病情很重。还有的人本来跟海鲜市场有关系,怕受歧视,会隐瞒病史。
偶尔有病人看别的病,妇科的、儿科的、外伤的……她尽量暗示别人:「你坐外面去吧,外面空气好一点。」有的病人听说了一点消息,愿意出去,有的不愿意:「外面冷,里面暖和。」她只能打开窗户通风,并给病人们发了外科口罩。她爷爷、她父亲和她,是三代党员,她相信官方通报的人不传人,但现实又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没过几天,1月13日,急诊科的两位护士确认感染。关秀丽从医院物资科抢来了N95口罩,让护士们都戴上,还有帽子。但穿的还是白大褂,有防护服,不能穿,她们收到指令,「不要引起恐慌」。
1月17号下了班,她没回家,去了其他医院。没有坐公交车也没有骑共享单车,怕车把手不干净,她走路,走到两站地外的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又去了湖北省新华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各个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医护们已经全副武装。她拍下照片,发给领导,没回复,又打过去电话,对方说:「你们自己看着办。」看着办,那就是可以了。她立刻通知护士们戴上面屏,穿上隔离衣。那时,红会医院门诊的病人已经占据了整条走道,排得很长很长。
1月18号小年夜,本是关家吃团年饭的日子。关家都在医疗系统工作,爸爸是军医,妈妈是护士,大姐在武汉市第八医院做医生,二姐在社区卫生站,哥哥在黄陂区第一人民医院,全家都在一线。他们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有问题,互相提醒注意防护。哥哥姐姐跟大家商量,团年饭不吃了。全家都同意。这顿饭在餐馆里交了押金,钱也不要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关秀丽的大姐,武汉第八医院的内科主任,在出诊时被感染,居家隔离后恢复,继续上岗。那是武汉封城前发生的事情。
1月中旬,红会医院已经有规定,病人一旦发热,只能送到呼吸科。但还是有病人被漏掉,去其他科室就诊,肿瘤科和内分泌科是重灾区。1月20号,钟南山在电视上第一次说可以人传人、有17位医护人员感染时,红会医院已经有医护确认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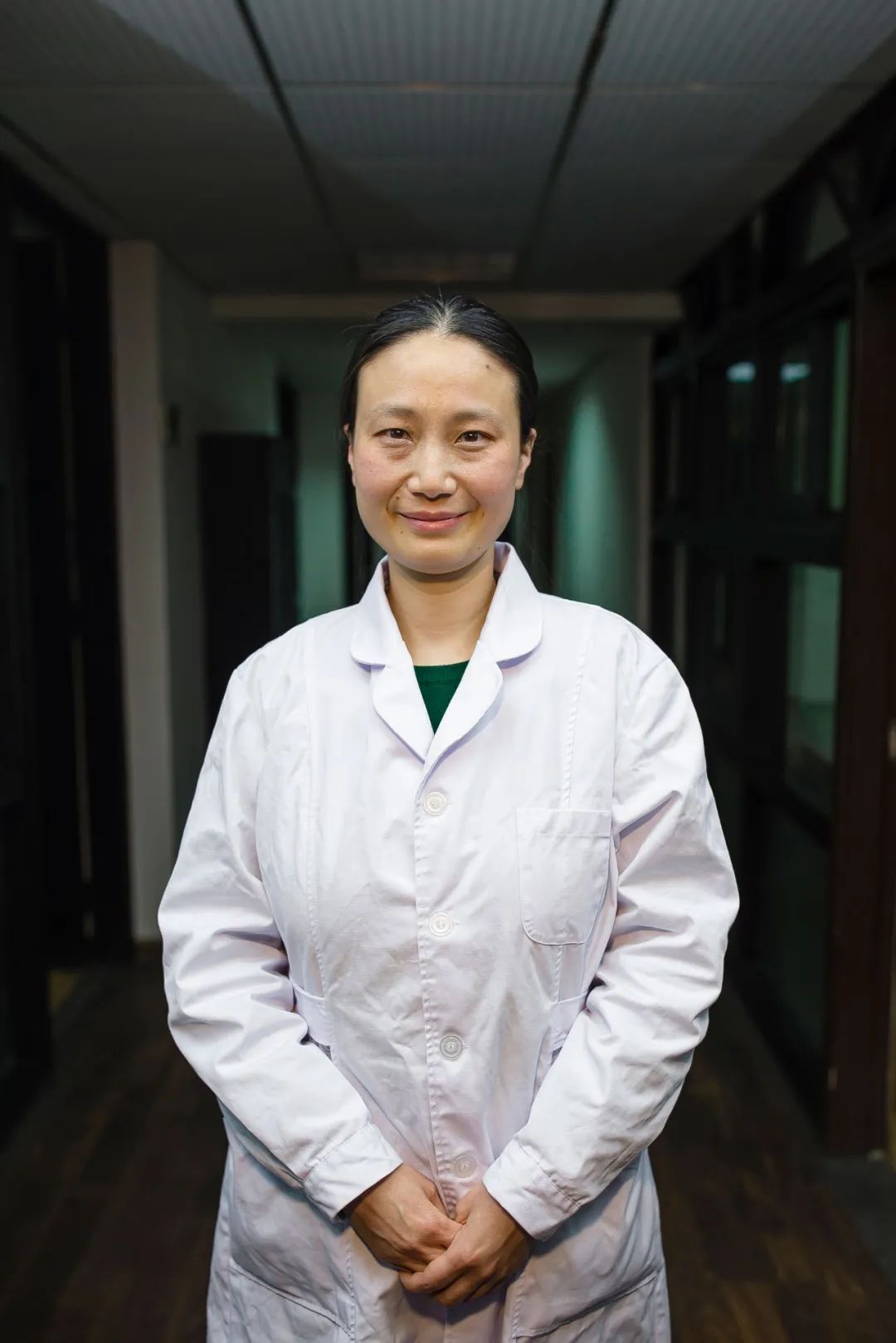
关秀丽
指定了一批定点发热门诊,就意味着——武汉另外几十家医院的发热门诊都不开放了,病人将高度集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最早一批被列为定点发热门诊的医院,如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都是二级医院,不管是人员、物资还是管理,都难以在一夜之间有序应对突然暴涨的就诊人群。
汉口医院急诊科主任胡红平无法忘记开诊第一天他走到门诊大厅时的所见:临时改建的空旷大厅,已经挤了上千人,下不去脚。第一个念头是万一发生纠纷,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保安,但根本找不到人。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王洁记得,所有病人都陷入了恐慌,不管新冠非新冠,全部涌进门诊,造成了更严重的交叉感染。
红会医院无疑是最惨烈的医院之一,门诊开放首日门诊量1700人,最高峰时2400人,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比协和、同济还多。关秀丽和她的同事们至今也搞不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也许是因为他们承接了协和转来的病人;也许是因为红会医院一直以「不拒绝病人」著称,120会优先把病人送到这里;还有人认为是消息在传播时出了问题,让病人们认为红会是唯一一间开放门诊的医院。
关秀丽的丈夫是湖北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他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1月21日的红会医院:因大规模病人的涌入而上了微博热搜。睡在过道的、躺在走廊的、哭的、吼的、闹的、下跪的病人,情绪失控的家属们,让整个医院场面失控。
按照诊治流程,轻症病人去看发热门诊,重症和危重症病人则送到急诊科。一两千人困在一个小院子里,要看病,要用药。保安不在,保洁也不在。大厅没有热水,门诊没有床位。开诊第一天,门诊部主任胡臻的口罩就差点被扯下来了,护士的防护服差点被扯破。现在的门诊台空无一物——因为东西都在那时被砸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里崩溃大哭。
医生王钧本是骨科主任,经过紧急培训,到发热门诊上岗。他说,当时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置身核爆现场:「你们如果感觉到核爆炸冲击波的力量,我们的感觉到你们的五倍到十倍,我们是承受第一波核爆的人。我们站在最前沿,是突击队,尖刀班。」
物资的问题首先浮现,平时运转顺畅的供应机制面对暴涨的病人,已经崩溃。
门诊医生生病,诊室缺人,胡臻给领导发微信请求增援,得到的回复是「自行调控」。后来她就放弃了,就那么站着,再也不求了。
急诊科向领导求助,收到的是两个字,「顶住」。「就像打仗一样,这里都要被敌人攻陷了,援兵还不过来,叫你顶住。」
急诊科的两位领导性格迥异。副主任吕希俊皮肤白净,性格沉静温和,经常从清早忙到凌晨,是个默默做事的老好人。护士长关秀丽则是典型的武汉女人,泼辣,利落,说起话来风风火火,想成的事不管怎样都得办到,她说,「要不泼辣点,工作也难得搞」。解决后勤问题是她的责任,她用尽方法,吵、哭,甚至是「偷」。
新冠病人缺氧严重,氧气像金子一样珍贵。红会医院有个制氧中心,每天生产的氧气有限,关秀丽就去门口守着、占着,一有氧气必须优先拉到急诊科。负责这件事的同事的电话号码,她背得烂熟。
管设备的、管物资的、管总务的,她和每个负责人都吵过架。疫情爆发前,她就从物资科抢了一批N95口罩;疫情爆发后,急诊科最初有两台空气消毒机,但病人太多,根本不够,管物资的同事在电话里说,「真的没有了,已经汇报了。」她凶回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在录音,你怎么样都给我搞一台来。」最后院感部门把儿科安在墙上的那台拆下来给她。心电监护仪本来有十几台,但根本不够,下了班,她和吕希俊把放在住院部大厅里还没有分配的心电监护仪全部「偷」回急诊科,还「偷」了好些个氧枕。病人太多了,氧气瓶再多也是有限的,氧枕好歹可以应急。护士问,这哪里来的?他俩说:「你不管,你先用。」
哥哥关秀文听到这些事迹,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可以想象,有可能。只要把东西搞走,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这是她做得出来的事情。」他也是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理解妹妹为什么会这么做。她是护士长,要保护好病人,也要保护好团队,不能让他们「裸奔」。
在极端有限的条件下,门诊和急诊勉力维持,也不得不因陋就简。传染病医院需要设置「三区两通道」,红会医院住院部改造时设置了,但门诊还没来得及做。每到饭点,门诊和急诊的医护就在污染区里用来换衣服的小房间里吃饭,脱掉隔离服的上半身,吃完再穿上。其实隔离服已经被污染了。但当时,他们没有更多时间也没有更多的隔离服可以替换。房间外就是拥挤的病人,咳嗽、打喷嚏、吐痰。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一切还都乱着。医院安排酒店时,在群里接龙报科室所需房间数,关秀丽没时间看手机,没有分到房间;去领饭,早已经过了饭点,剩的饭不够急诊科吃。关秀丽搬个板凳坐在五楼,心里绝望,哭了起来,觉得眼前无路,没有饭吃,也没地方住。靠眼泪,她最后得到了三个房间。


医院门口的小公园里,一树一树的花都开了,关秀丽拿着手机,拍下那些花,又惦记着给流浪汉送点吃的。流浪汉声音低沉,跟她说「谢谢」。那些时刻,她感觉自己「全好了」,但又知道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创伤需要去抚平。最实在的,急诊科的19位护士有8位病倒了,她们需要时间恢复。
爸妈是医生护士,哥哥姐姐都学医,从小,关秀丽就觉得学医蛮好,自己就应该做这个。中学时,她在家偷偷戴妈妈的护士帽,是时兴的燕尾帽,对着镜子照,觉得好得意,好漂亮。18岁进了医院,没几年就拿了技术大比赛的标兵。2003年SARS的时候写了请战书,但那时武汉疫情不严重,没有太多波澜,疾病好像就过去了。2019年,她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护士。这么些年,她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搞不定了还可以打电话找领导,再不行就请专家会诊,总能搞得定。
她的性格也经得起急诊科的摔打,坚硬、大条,没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受伤。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一点也不娇贵。小时候高烧39度,爸爸照样送她去上学。哥哥说她是典型武汉女性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心肠好的人。」结了婚,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和很多武汉女性一样,喜欢自称「老子」。丈夫是一名记者,她叫他「无用书生」,换个灯泡,都是丈夫扶着梯子她上去。
在急诊科里没日没夜的那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关秀丽的丈夫实在担心,给她送饭,约在她住的酒店门口。是她走错了路,却冲丈夫发了一通火。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有泪痕,不住说,「太多病人了,太乱了,太累了」。丈夫说,结婚十几年,她几乎没有在他面前脆弱过,因为她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能哭,以哭为羞。但那时,她忍不住了。丈夫说,很想给她一个拥抱,但只能保持一米的距离。
那种「总能搞得定」的感觉被打破了。在急诊科22年,关秀丽早就接受了那些意料之中的死亡。那些注定的、无可挽回的,她会安慰自己:你尽力了。但这一次的许多死亡,本不该发生,「可惜、难受、心痛」。
在医院,急诊科从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门,效益也不高。但红会医院急诊科是一个骄傲的集体,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希望为病人提供最需要的帮助。红会医院是120、110定点医院,110送来的,经常是乞讨的、流浪的、捡垃圾的「三无人员」。急诊科的医护给这些「三无人员」看病,还帮他们找家属,送给他们衣服,自费给他们买饭。有时候流浪汉说不想喝水,想喝可乐,他们觉得好笑,但还是会满足。
陈楚楚说,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对病人还是要温暖一点。如果用那种很嫌弃的心态对他,觉得好烦好臭,上班不会很开心。你如果自己把心态转过来,他很可怜,给他买口吃的、买口喝的也没有什么,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自己上班也轻松一点。」
她不以忙、累为苦,经历过这次疫情,陈楚楚申请支援ICU。目睹比往常多许多的病人故去,她伤了心,每晚靠安眠药入睡,还总是做梦,梦中是同样的内容——自己跪在地上抢救病人,她觉得好累,不断重复着抢救的动作,不断有人在喊她:护士,护士,护士。二月中旬以后,急诊科的工作不再像刚成为定点医院时那么疲惫,但她还是无法解脱,「可能我潜意识希望把那个人救活。」
还有一位护士跟关秀丽提出辞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下了班在酒店大哭了一场,给关秀丽发微信说不干了。她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绝望无助的眼神。每一双眼睛都那么看着她。「绝对不是累,是心痛,是无能为力。」关秀丽给她打电话,聊到凌晨两点半,算是说开了。隔三差五,又在酒店给她们煲汤,她想,要把年轻护士的情绪照顾好。
急诊科副主任吕希俊与关秀丽同龄,也是41岁,头发已经灰白了。摘下口罩,胡子也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来得及刮。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流眼泪,说不上原因。他说第二批、第三批的定点发热门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创伤。」
2月17日,《人物》第一次见到关秀丽,她在红会医院的会议室里一坐下,就叹了一口气:「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再让我流泪,不可能了。」
那些惨烈的场景,关秀丽再说起,语气并不惊心动魄。听来会觉得,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勇气,只是不得不去做。分配,决定,目睹脆弱与死亡。但也是她,和与她类似的武汉医护工作者,扛起了这漫长的30天。
疫情过去后,你们想做点什么?
关秀丽、吕希俊、陈楚楚……这些在这个急诊室里度过了十多年时光的人,说出来的都差不多,「就像平常那样上一天班,穿普通的白大褂,戴普通的口罩,和病人普通地交流。他不用担心来医院会死掉,我也可以给他提供相应的护理和治疗。大家就这么平平常常地,他治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该下班就下班,我想过一天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