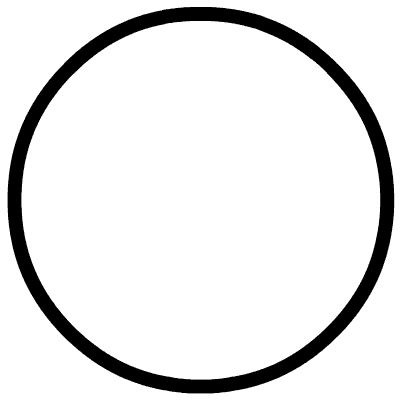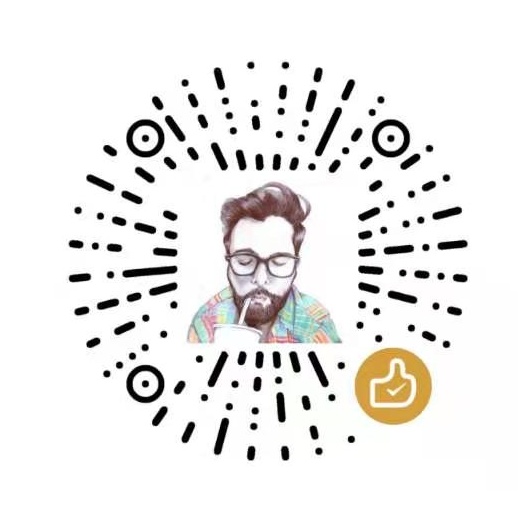去年以来的疫情,深刻影响了我们每一个海外学子和背后的每一个家庭,谱写了一幕幕海内外江山儿女同气连枝、共同抗疫的感人篇章。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调整步伐,重新出发的机会。
走过长路,才会相信勇敢的人会更勇敢。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迎来了满怀希望的牛年。在这春生万物、向新而生的季节,江山市留联会开通了“山海鲸2021”公众号,作为记录江山籍海内外学子故事和相互信息交流的一个小园地。欢迎各位鲸友多多参与,常来发声,让“山海鲸2021”成为大家心灵交流的温暖港湾。
本期我们推出现居纽约的陈小爱博士的《一个菜农女儿的耶鲁留学路(上)》,让我们跟随她的记忆,一起去回看历史,回味心路!
欢迎更多的海外学子和亲友们分享你们的人生经历与喜怒哀乐!
作为美国华裔家庭的第一代移民,回想起26年前第一次到美国留学的经历,恍若隔世。或许我们的后代并不会知道我们当年初到一个完全陌生国家的兴奋、懵懂与不安,这里留下一些对那段人生轨迹的记录,权作对逝去时光的一个怀念。

1984年,江山中学原校址,陈小爱初中毕业纪念照。
时间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和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一大批年轻学子怀着去先进国家学习深造并开阔眼界的梦想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开始人生新的旅程。

1991年,陈小爱在北京大学。
我,一个来自浙江小县城江山的农家子弟,从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起,也被这股风吹到了。但是,这个梦想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显得非常的不现实。
那个时候要出国留学,第一是家庭必须有海外关系,第二是出国前要付一大笔培养费(本科毕业1万,硕士毕业2.2万)。这两个条件,我都不具备。我父母是半文盲的菜农,而且我是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那个,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近60岁,靠种菜为生并供养我上大学极其辛苦。

1991年,陈小爱在北京大学。
小时候父母和我最大的愿望是我能跳出农门,有个“铁饭碗”。所以初中毕业时,我曾试图报考中专,幸而在当时的江山中学教务主任王兴盛老师的鼓励下,选择了读高中,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上大学时知道同学里有不少家庭条件好的在考托福考GRE,然后大学一毕业就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了,但我没有这个条件,就只能尽自己的努力,寻求在国内最好的深造条件。因此,1991年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时候,我考取了当时中国遗传学领域最好的研究所——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1991年,陈小爱在北京大学毕业。
到了复旦大学以后,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并接着在遗传学研究所直升了博士研究生。期间,受环境的影响,出国留学的念头依旧有。那时候国家已经放宽出国留学政策,不需要侨属关系了,而且博士毕业也不用再交赔偿金,所以我的想法是博士毕业以后去美国做博士后。
没想到出国的机会比我计划的来的更早一些。
1994年9月,我开始博士一年级的学习。我的博士导师是赵寿元教授,当时国内著名的遗传学家之一,曾经担任过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主席(1998-2003),是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中国人。另外一个导师是李昌本教授,当时刚从美国耶鲁大学回来,年轻有为,思想也很活跃。进实验室不久,李老师就提到他和美国耶鲁大学以及英国的一个研究所正在申请美国McKnight Foundation的一个全球合作科学研究项目。
当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的三位合作教授来上海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年龄最大的是Frank Richards教授。他当时65岁左右,矮矮胖胖,花白头发,总是笑容满面,第一次见面就让人特别温暖;Frank出生于英国,曾经服务于英国皇家空军,在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都很有建树。年龄最轻的是Scott O’Neill,澳大利亚人,当年才35岁,在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Scott英俊帅气、才华横溢、待人非常和气,眼神里时不时还有一丝调皮。第三个教授叫Serap Aksoy,当年她40岁,来自土耳其;Serap美丽优雅知性,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女科学家可以和时尚的穿着打扮共存。
三位教授到复旦访问的第一天,李老师把我们实验室所有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叫去和他们见了一个面。见面会上他们介绍了自己以及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我也问了几个问题。
三位教授都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还陪着他们逛了逛上海。第一次用英语和老外直接进行交流,还多少有点紧张,尤其在逛街的过程中,很多意思都不知该如何表达,但是这给了我一次极好的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几天后送走了三位教授,我的生活回归正常。

1994年,三位教授第一次到复旦大学,左二是Frank,左三是Serap,右二是Scott,陈小爱在Serap和Scott之间。
转眼到了1995年上半年。一天,赵老师和李老师跟我说,McKnight基金会的项目申请成功了,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由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帮助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第一期要从复旦遴选三个博士生,两个送去耶鲁,一个送去英国的研究所。因为三位教授来复旦时对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认为我学术和英语都非常突出,而且沟通能力也很好,因此我被选为要去耶鲁大学联合培养的两个博士生之一。也就是说,我下半年就可以去耶鲁大学学习了!
我兴奋极了。尽管上大学以后,我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了,但对远赴重洋的求学生涯仍然非常向往。更何况,要去的是举世闻名的耶鲁大学啊! 我的梦想要实现了!
记得耶鲁教授们来上海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几本耶鲁大学的画册,我拿到一本。那本画册里有哥特式的图书馆,绿草茵茵的大草坪,被绿色爬山虎覆盖的学生宿舍和红墙……我曾经一遍一遍地翻看,而现在真的很快就能走在画册中的风景里了。

耶鲁大学鸟瞰图。
1995年9月7日,我坐上了从上海虹口机场到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飞机上冷气开的很足,会很冷。当时上海还是很热的夏天,我穿了很薄的套裙,一上飞机还要了带冰的饮料,结果很快就晕机。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赶快找空姐要了毯子、热的饮料,才慢慢缓了过来。
当年的飞机,加一次油无法从上海一直飞到纽约,所以我们的飞机是经停阿拉斯加的首府安克里奇再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
到了纽约是夜里。Serap 派了她先生来接我,在耶鲁交换的另一个复旦的学生(周师弟)随车一起来接我,因为Serap的先生不认识我。
纽约肯尼迪机场到耶鲁大学所在地的New Haven大约开车1个半小时。因为是晚上,又一直在高速上开,除了路什么都看不到。一直到下了高速,路过New Haven市区的时候,我才看到了一些房子。当时最惊奇的是看到路边停着很多汽车,因为上海那时候很少有私家车。
当时的打算是那天晚上先去Serap家里住一夜,所以我非常好奇Serap家是怎么样的。我以为她会住在New Haven市区,结果我们的车子并未在New Haven停下来,却越开越往偏僻的地方走,到后来,我发现我们完全是在有很多参天大树的森林里的小路上走,不禁有点奇怪。为什么Serap要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当时想当然地以为,美国这么发达,难道不应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么?
终于到了Serap家,在一片树林中,一个小小的房子。Serap欢迎了我,说今晚我睡她大儿子的卧室。我因为时差,一夜睡不安稳。第二天早早起床,才看到了她家全景。

类似Serap家(网络照片)。
她家房子是大平层,大概150平米左右,加一个地下室。一楼有三个卧室,她夫妻和两个儿子一人一间,怪不得我来后,她大儿子就要去和小儿子挤一下了。她家的地下室被他们改造成了一个酒吧,还有书房和办公室。房子建筑虽然不大,但占地很大,差不多有5500平方米,除了围着房子的前后院有草地,剩下的都是原始森林一般,参天大树覆盖,和邻居离得很远。
后来我很快就知道,美国有钱人往往都住郊区,因为房子大,学区好,环境好。因为家家户户都有车,公路到达每一家门口,所以不存在不方便。除了极少数城市(比如纽约曼哈顿),大部分城市市区都是穷人才住的。Serap当时是助理教授,她先生是一个公司的工程师,算是中产吧,他们的这个房子大小和位置与他们的收入很般配。

类似Serap家(网络照片)。
吃了一点我很不适应的早餐后,Serap开车带我去了耶鲁大学的实验室。从她家到实验室开车大概15分钟。实验室不大,当时只有一个博士后叫Sukanya,印度人,大概30出头,有一个才一两岁的儿子。Sukanya个子很瘦小,一头短黑卷发,非常幽默友好。
Serap买了一盒甜甜圈(Dunkin Donuts)带到实验室的小餐厅(lunch room)。小餐厅在实验室的下面一层,属于这两层实验室共用,有微波炉、炉头、烧水壶、冰箱等基本厨房设施,大家可以在里面吃东西聊天。那天早上,大概事先通知了我要来,周围几个实验室的教授学生博士后等有不少人在,Serap一一为我介绍。我这才搞清楚,原来Scott的实验室在小餐厅所在的这一层,Frank的实验室和Serap的实验室在同一层面。那天我也再次见到了Frank和Scott,他们都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
那一天,印象中就是Serap不断地给我介绍周围实验室的人。到了下午,我的时差反应上来了,开始晕晕乎乎的,好困啊,但Serap好像没有要送我去休息的意思,我只好强忍着到晚上和Serap以及Scott实验室的人一起吃了晚饭,她才把我送到了我的临时住处。

耶鲁大学校园一角。
到达耶鲁大学的第二天,我便正式进入Serap的实验室开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Serap没有给我任何倒时差的时间。这个,一方面是美国人普遍比较精力旺盛,时差对他们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另一方面Serap认为只有马上投入到正常的学习工作的节奏中才更有利于我调节时差。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好方法,直到现在我在中美之间飞行已经能做到第二天就正常上班生活。
Serap的实验室隶属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属于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从外面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楼和医学院大楼并不相连,但是通过地下通道,可以从一个大楼直接到另一个大楼的任何地方,这点在北方漫长的冬天给教职员工带来很多的方便。除了大楼之间的连接,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院也分享各种科研资源,比如图书馆、学术会议、仪器设备等。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医学院图书馆查资料,参加医学院学术会议等。Serap本人也在医学院有教职,给医学生和研究生上基础课。

耶鲁医学院正门。
当时Serap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非洲昏睡病。非洲昏睡病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才存在的一种由锥虫引起的人类疾病,它通过一种会叮咬人类并吸血的采采蝇(舌蝇属)在人群中传播。被这种特定的锥虫感染后,患者先会出现发烧,头痛,淋巴结病等症状,进一步影响到神经系统,出现昏睡、行为认知障碍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会存在生命危险。
我到美国实验室后的第一个感想是实验条件真好。去美国以前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实验室在国内是领先的,但是我们做分子生物学实验最常用的一些塑料试管、培养皿、微量加样器头等,是要清洗灭菌再重新使用的,而在耶鲁实验室,这些都是一次性的,感觉是无限制地供给。医学院大楼内就有一个像超市的小仓库,我们推着小推车去,拿走需要的用品,刷一下实验室的卡就可以了。我记得第一次是前面提到的博士后Sukanya带我去的,我和她说,这简直像在逛街购物!
现在,中国的实验室条件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像复旦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在国内顶级的研究单位,据我所知,在仪器和耗材方面的供应和一般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已经没有区别。

陈小爱在耶鲁学习时的实验室一角。
第二个感想是耶鲁大学的学术交流可真多。从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到教授们,从校内自己人到请来的世界各地学者,都会把他们正在做的最新研究结果在各类学术会议(seminar)里和大家交流。医学院加公共卫生学院,每个星期都有学术会议,所有人都可以去听。这类学术会议如果是在午餐时间,一般都会提供简单的午餐,最典型的是比萨饼加饮料。每人拿块比萨饼,一边吃一边听讲座,物质和精神食粮都有了。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及时知道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阅读文献和学术交流,两者缺一不可。我在耶鲁的时候,要阅读最新文献非常容易,因为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会订阅重要的学术期刊。去图书馆找到发表论文的那本期刊,复印一下就可以了。而当时在国内却不行,因为那时订阅国际学术期刊,一来很贵没有经费,二来邮寄时间很长。所以我初到耶鲁,感觉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自己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知识。
如今过去了20多年,感谢互联网的发展,学术期刊都已数字化。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原因,国际学术会议都已经有不少搬到了线上。这些变化,使得在国内的学者可以非常容易地接触到最新科研发展,全球化已经并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
第三是我看到了科学家对科学的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点我的导师Serap令我印象深刻。她来自土耳其,是个学霸,家教良好,会弹钢琴。到美国以后,以她的聪明才智,她大可以选择那些容易赚钱的行业,但是她却一心一意地爱上了科学研究。在美国,从个人收入来说做教授只能算是中产,但是必须付出超常的工作时间,因为在科研领域中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发表文章和申请经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的我,对于美国实验室财务上是怎么运行的,根本没概念。后来我知道,在美国要运行一个实验室,教授自己必须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因为教授自己的工资、实验室博士后技术员等的工资,以及做实验需要的仪器耗材等,大部分都要靠教授自己去申请。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那时候我发现Serap 有时会去买彩票。有一次,我问她,你要是彩票中奖了,你准备拿这些钱干什么?我知道一般的人要是中了彩票肯定是用来买大房子周游世界等,但是出乎我意料,她说她要拿这些钱来支持自己的实验室做更好的研究。她接着不由自主地跟了一句:I love science(我热爱科学)!这句话,以及她当时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科学家,她对科学的热爱也影响了我一生。
当时Serap的两个儿子,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她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在耶鲁的时候,她先生还遭遇了被裁员。然而,她每天都是优雅美丽、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实验室里,像一个儿童在游乐园里,乐此不疲。
我到耶鲁的时候,因为在复旦已经把博士学位要修的基础课都修好了,所以在耶鲁大学完全集中在做学位论文。在耶鲁的两年多,除了最重要的节假日我会放假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实验室。早上去经常要晚上才回家,周末有时也会去加班,因为周末如果不去照顾一下培养的细胞,会影响下一周实验的安排。
大部分时候,实验工作是很枯燥的。如今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那时候的自己,一心只想好好做课题,别的事情几乎很少考虑。成长于80年代的我,从小就以“居里夫人”为榜样,一心一意地觉得长大以后做个科学家,探索生命的奥秘是我人生唯一的使命。从后来的人生来看,这种想法当然过于乌托邦,但也是这样单纯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在一般人看来枯燥辛苦的攻读博士的那段时光。
科研工作不仅枯燥,更具挑战的是必须接受一次次的失败。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实验结果都不理想:不是实验因为各种技术问题不成功,就是实验结果和我们的设想不一致。这时候就要不断地改进再试验,直到拿到满意的结果。
在耶鲁的几年里,也有科研进展顺利,比较激动的时候。我仍记得第一次手工DNA测序成功,看到X光片上那一排排整齐的条带,我高兴地手舞足蹈的样子;我也记得,做southern杂交,看到符合自己预期的条带出来时的兴高采烈;还记得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时的兴奋……
在实验室有一个放松的时刻,就是每周五下午四点,Serap实验室和Scott实验室会在我们的lunch room有一个联合的Happy Hour 。两个实验室会轮流买一些食物和饮料,包括啤酒,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们,操着各种各样口音的英语,天南海北,聊天聊地。这算是枯燥的研究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吧。
如今的我已经不在科研的第一线,但是我从来不后悔年少时的立志,以及在实验室度过的那十几年的时光……
–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陈小爱,1970年生,6岁上学,浙江江山人。先后就读于江山城东小学、江山中学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5年被复旦大学派往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获遗传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复旦大学、康奈尔大学从事生物科学研究,2006年起转行做教育和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现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系科研基金管理经理。
在1994年—2006年的科研生涯中,共有11篇科研论文(其中6篇为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科研专业期刊上,其中包括国际公认的顶级科研期刊“Molecular Cell”和“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人生信条:科学 理性 温暖



正月十五人月圆
元宵佳节香气飘
衷心祝愿海外学子们
学业有成
事业进步
祝愿你们的父母
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PS: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辑 | 汪雪涯

来源:江山市留学人员和家属联谊会

请长按下方图片
识别二维码 关注江山人网